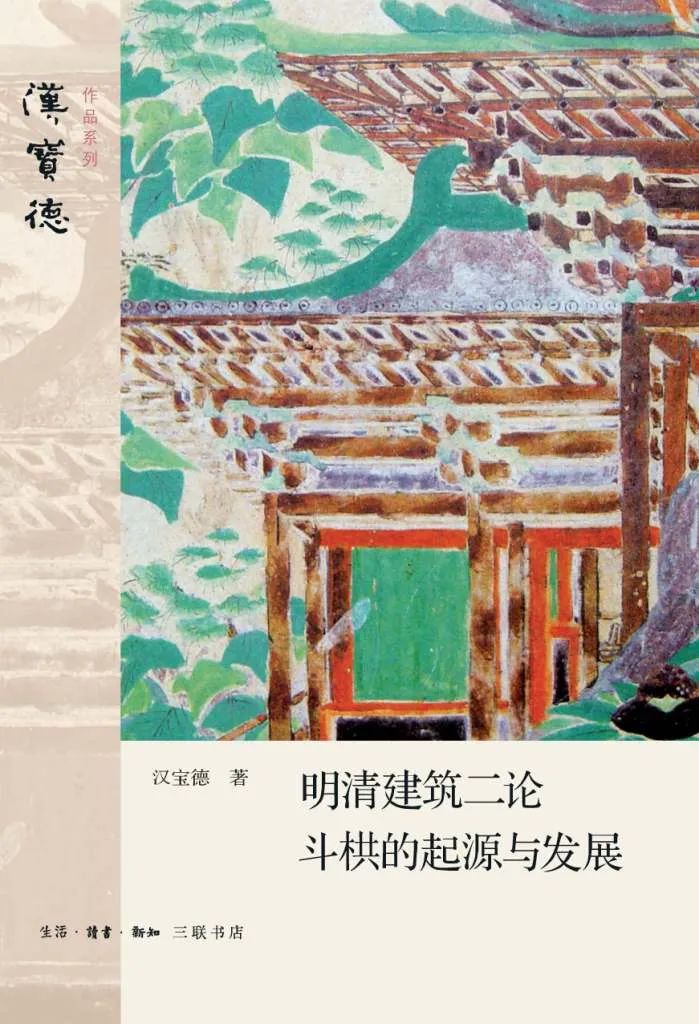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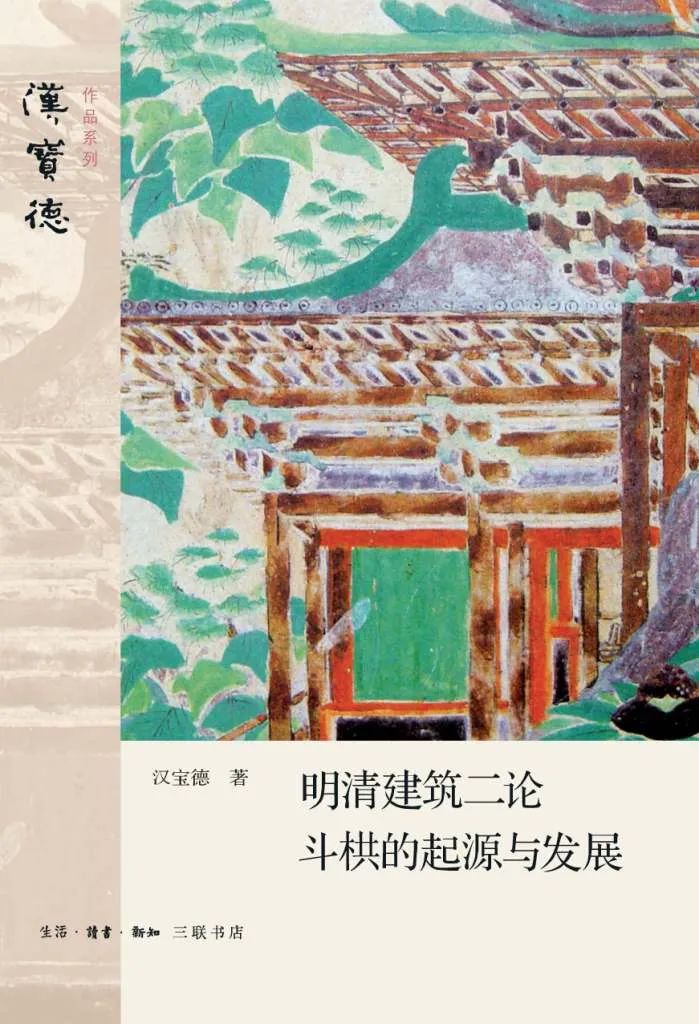
原创 陈志华 读书杂志
编者按
1991年,建筑学家陈志华写了这篇热情洋溢的书评,推介台湾学者汉宝德的一本小书——《明清建筑二论》。陈志华说这是一本“论战”的书,而论战的对象,正是自己的老师林徽因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绪论》。汉宝德在《二论》中提出了建筑史学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评定建筑的价值标准,另一是关于建筑史的学术体系。三十年一倏而过。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甚至不能说已经做了深入的探讨”。
读《明、清建筑二论》
文 | 陈志华
(原载《读书》1991年第1期)
汉宝德先生是一位探索的、挑战的、敢于走自己的道路的建筑学家。他在建筑理论、建筑创作和古建筑保护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台湾的建筑学界很敬重汉宝德先生,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写的两本小册子,《明、清建筑二论》和《斗栱的起源和发展》,被一致认为是开辟了台湾建筑学术史的著作。今年我第二次到台北,有一天跟《空间》杂志社的朋友们座谈,我说,大陆在中国建筑史方面有很优秀的人才,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学风太封闭,经历过这么多的社会变化和思想激荡,居然没有出现一篇讨论中国建筑史的史学、史观、史法的文章。一位朋友立即问我,看过汉先生写的那两本书没有。我听说过它们的重要意义,但那时候还没有读过。我想,非赶快读一读不可了。开云体育app

《明清建筑二论·斗栱的起源与发展》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4年出版
汉先生送过我几本书,却偏偏没有这两本。我在书店里也找不到,于是直接到了出版商那里,总算得到了一本《明、清建筑二论》。但细细地读它,却是将近五个月以后的事了。读着这本书,我感觉到一种很特殊的享受。它谈哲理,深刻,却不故弄玄虚;它谈历史,广博,却不炫耀知识;它说理透辟,却又洋溢着人情,触摸到心灵底处。而且文笔简练潇洒,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很复杂的事情。当然,更给我享受的是时时涌出的新异的见解。
虽然在更多的学习和思考之前,我暂时还无力全面地介绍汉宝德先生,但我却急于把这本小册子介绍给大陆的建筑界,因为我们知道得已经太晚了。

汉宝德(来源:thepaper.cn)
《明、清建筑二论》是一本论战的书。论战的对象是林徽因老师的《清式营造则例·绪论》,论战的题目是明、清建筑不如唐、宋建筑吗?汉先生的论点是:一,林老师“所留心的中国建筑的范围也许太狭窄了一些”,即只从官式建筑立论,既没有看到中国建筑的地域性和地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没有看到朝野建筑观念的对立;二,林老师受“结构机能主义”的束缚,论“由南宋而元明而清八百余年间,结构上的变化,无疑的均趋向退步”,从而判定明、清的建筑整个儿是“低潮”。主要针对第一点,汉先生写了《明、清文人系之建筑思想》,对第二点,他写了《明、清建筑的形式主义精神》,合在一起,就是《二论》。开运app下载(kaiyun)
《二论》以明、清建筑为题,其实涉及到了中国建筑史学,包括史观和史法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价值标准的问题。汉先生主张“跳出结构至上主义者的圈套……探究我国建筑在形式以外的成就,以及它怎样满足了当时社会群众的需要”。汉先生把满足当时社会群众的需要作为评定建筑的价值标准,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但能摆脱形形色色的机能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且能把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真正沟通起来;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建筑史的外部与内部的学术结构的。汉先生说:“建构一个社会史、建筑史、考古学三方面融通的学问框架,而汇成于我国文化史研究的大业中。若不如是想,则我国建筑史的研究,充其量只是技术史的讨论,或者考古的调查,枝枝叶叶,零零星星。等而下之,研究之成果被执业建筑师所剽窃,或径用为抄袭之蓝本。”汉先生写《二论》的时候,台湾所能见到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著作,仅仅只有一套《营造学社汇刊》,对大陆上学者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一无所知,不过,即便如此,他的论点仍然是有现实的意义的。那二十年里,有人把“理论联系实际”阐释为“建筑历史为建筑设计服务”,迫使我们一些人做了些“等而下之”的工作。而把建筑史研究汇入到文化史研究中去,也没有找到门路,倒是险些儿汇入到简单化了的社会发展史即阶级斗争史的模式里去。我说汉先生提出来的两个问题有现实意义,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甚至不能说已经做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来源:douban.com)
就明、清建筑的评价问题,汉宝德先生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要有地域观念。不能把中国建筑看成简单的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地域现象表现在建筑上极为明显。”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南方,明清两朝,江南一带实际上扮演着主角。所以,评估明、清的建筑,不能再限于北方官式建筑的如何如何,而应该看到江南一带地方建筑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代表着明清建筑的进步。
我们不难给汉先生的这个论断找到强有力的证据。造园艺术不用说了,就建筑来说,明清以来,在北方建造宫廷的著名的大匠们,都来自南方,建筑装修中大量使用了苏州和扬州的做法和产品。也正是在南方的城市和乡村里,这时候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和相应的型制,在北方却没有或者很少有。南方建筑的装饰工艺,如木雕、砖雕和石雕,精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皇家的建筑,而且富有创造性,不僵死为几种模式,如北方官式建筑那样。跟这些情况相应,在南方产生了初期的、片断的建筑和造园理论,而北方官家却只有典章制度。
第二,所谓地域差别,主要不是自然条件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人文的差别,传统的差别。汉先生说,明代的江南“渐出现资本社会之雏形,产生中产知识分子的阶层,在生活的需要上与情趣的捕捉上,自然发展出异乎以北方(官式)为中心的正统建筑”。他在这里已经隐隐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明清之间,江南建筑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些特色,比起封建主义的正统来,它们显然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这是明、清建筑优于宋、元建筑的本质原因。
多半是因为当时缺乏资料,汉先生不得不把明、清建筑的进步局限在江南文人对建筑学的创造性贡献上,主要是这篇论文的题目标示出来的“文人系之建筑思想”。
作为文人系建筑思想的代表,汉先生提出了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和李渔的《闲情偶寄》,此外还有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园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来源:douban.com)
在引述了《园冶》中的“三分匠七分主人”那一段文字之后,汉先生出人意外地说了一句很“高调”的话。他说:“这一段说明是南方传统的一个宣告,它代表的意义是向已推演了上千年的宫廷与工匠传统挑战,其历史的重要性不下于欧西文艺复兴读书人向中世纪的教会御用工匠传统的挑战。这是建筑艺术知性化的先声。”他随后指出了这段文字的三个要点:一是肯定了“能主之人”的主导作用。这能主之人既不是主人,又不是匠人,而是建筑师类型的人。二是“提出建造之最重要的部分是今天所谓的基地计划,不是细巧的雕凿与梁柱的排架。”三是“要解除制度与匠师的束缚,以创造舒展灵性的新居住环境,即“得体合宜,未可拘牵”。这些思想不但大大优越于为帝王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且因为计成不束缚于宗教,不服事于统治阶级,脱离了早期的象征性,只从生活出发,与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建筑理论远超过欧西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师。”
所谓从生活出发讨论建筑,它的一个含义是,以计成等人为代表的文人们真正讨论了建筑的“设计原理”,也就是“建筑学”,而不是《清式营造则例》和《宋营造法式》那样的“匠法”。汉先生认为,那些“与欧西中世纪的僧侣们并无不同”的读书人整理出来的“匠法”制度,“有时不但不能增长匠师的创造力,反会扼杀进步的生机”。
显然,汉先生不是从理论体系的完备和论述的严整来比较江南文士和欧西文艺复兴建筑家的,他说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明清之间渴求性灵解放、敢于向千年正统挑战的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再去看一看欧西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家如阿尔伯蒂的著作,就会对他的“言必称希腊罗马”,孜孜于制定僵死的模式教条,觉得不是滋味了。
关于江南文士在“设计原理”中表现出来的“敏感性”,汉先生列举了四大项:一、平凡与淡雅,二、简单与实用,三、创造与求新,四、整体环境的观念。确实可以说,这些都带有新兴资本社会的色彩,和封建的正统建筑观相对立。汉先生正是从这种对立下手来评述它们的。受到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只能介绍汉先生对这四项敏感性的正面意见。
平凡与淡雅,这是江南士人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在与宫廷文化和匠人传统对立中形成的。汉先生说:“平凡淡雅的极致就是一种处处适当,无不舒贴,然亦不过份的精神。所以外国建筑所讲究的权衡不一定是美的标准,也是善的标准。”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谈房舍设计,归根结蒂一句话:“房舍与人欲其相称”,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谈楼阁设计,强调的也是“宜”。李、文、计三个人对素木、粉墙、青砖、乱石和纸的质感和色彩都有精心的鉴赏和品味,汉先生说:“这种对朴实的材料的爱好,是高水准建筑的起点。”这些人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是精洁潇洒,并不喜欢太多的字画装饰,即便是一时之绝。汉先生评论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人建筑家是一些敏感而有充分设计头脑的人。他们不但有独特的审美见地,而且有很现实的精神,能解决不同方向的问题。对材料的质感与空间比例的欣赏……是属于平民的与知识分子的手法。”

李渔《闲情偶寄》(来源:auction.artron.net)
与淡雅的审美观相联系,简单与实用是这些中产阶级思想家们的基本要求。汉先生说:“大胆的丢开宫廷与伦理本位的形式主义,又厌弃工匠之俗,故很自然的发展出现代机能主义者的态度。”机能就是功能,这是两部官家的大典籍都“绝无一字谈及”的。而这些文士却讨论建筑群的配置原则和方法,不同功能建筑物的设计和使用,以及如何应付外在的物理环境等等。例如,文震亨详细地讨论了浴室设计,考虑到给水、排水、锅炉房,严寒季节如何使用,并且如何可以省钱省力。他还谈到“丈室”的设计:“丈室宜隆冬寒夜,略仿北地暖房之制,中可置卧榻及禅床之属。前庭须广,以承日光,为西窗以受斜阳,不必开北牖也。”李渔也提到储藏室的重要性和配置原则,甚至设想如何处理便溺。为室内空间设计,计成改变了官定的构架方法,他突破了用一列构架形成长方形房子的僵化模式,“几乎什么奇怪平面的房子都能做出来”。汉先生很重视最后这一点,所以对林徽因老师说的,中国建筑在技艺上“登峰造极,在科学美学两层条件下最成功的却是支承那屋顶的柱梁部分,也就是那全部木造的骨架”,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因为正是那个骨架,限死了中国建筑的内部空间,从而也限死了外部的体形。
明末清初,江南文士在雏形的资本社会关系的影响之下,大多有很高的创造与求新的自觉性。汉先生列举了三点理由,说明为什么与文学、艺术相比,历来在建筑上创新意识十分薄弱,抄袭几乎成为常规。然而,李、文、计这些文士,却勇敢地突破传统,大标创新。李渔激烈地攻击“法某人之制,遵谁氏之规”的陋习,他说:“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汉先生认为,李渔和他的同代人之所以能有这种意识,是由于他们的“物质主义精神”,使建筑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汉先生说:“只有物质主义的现世精神方能促使建筑不断因生活之需要而创新,明清之间的文人在居住环境有现世的觉悟,其要求推陈出新的呼声甚高,而难能可贵者,为此等知识分子有创新的要求,而无现代商业社会的现世主义者的奢侈,肤浅的纯官能享受之作风。”所谓“物质主义”,其实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有所避讳的说法,这是我们都能理解的。在物质主义精神作用之下,李、文、计等文士在讨论建筑和园林的时候常常采用经验的机能主义的方法。汉先生认为,经验的机能主义会渐渐发展成精神的机能主义,“一个时代的建筑思想如能透出精神的机能主义的趋向,就能产生真正的建筑论。”
中国的文化一向崇尚自然,但汉先生认为,从北宋到南宋,艺术家对自然的心理关系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就是“在艺术家心目中之自然,由天生之自然转变到人为之自然”。这个转变,开辟了环境设计的契机。我国的环境设计概念在南宋时已经铸成,远远早于西方。但中国的环境设计,又不是“设计自然”,以人工去设计自然,就是用人类的头脑与上帝争衡,必然要走入歧途。明清之间的文人的设计环境,是剪裁和选择自然,利用自然。汉先生说,这就是“通过建筑的方法去利用上帝的手笔,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他引用了计成关于“因”“借”的那一段话作为印证:“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他说,这正是现代建筑师们苦心孤诣以求到达的佳境。
论述了上述四方面之后,汉先生已经证明,从观念上说,明清之间的建筑思想比起以前的来是进步得多了。汉先生说,那些零零星星的见解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分析这些见解,“不但可以补足我国几千年来建筑思想的空白,并且可以把我国建筑史的系统重新加以划分。”他写的是对明清建筑的评价,想的却是整个中国建筑史。

李渔的芥子园(来源:ctrip.com)
但是,为什么江南文人没有产生真正的建筑师,也终于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建筑学来呢?汉先生说:“真正的建筑学是要在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生根的。因只有知识分子有治学必要的智慧,以及合理的思考方法。只有他们是肯脚踏实地做切合实际的思考,也只有他们拥有敏感的禀赋,可以为艺术的创造。”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有根本性的弱点,妨碍他们成为建筑师和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汉先生列举了两条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文化中过份的理想主义与过份的现实主义之冲突所造成的。因为健全的建筑学必须产生在健全的、发展均衡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文人们不是崇尚自然,标榜无所事事的闲情逸致,满足于茅屋三间,就是忙忙碌碌,为做官而善于折腰。读书人折腾于两者之间,无法安于现实,“建筑在士人阶级中,是这种独特的心情的矛盾下的牺牲品。”强大的官本位文化,使读书人不可能与官家脱离关系,从事专业的建筑学,甚至连文学家和画家都没有专业化,而是由官僚或准官僚兼任的。官僚可以兼任文学家和画家,却实在兼不了建筑师。
第二个原因是,文人的建筑思想中的敏感度,直接来自文人的艺术:文学、绘画与金石等。汉先生说,“文人艺术的性格属于心性之陶冶,……是在现世残酷的生活中一种求慰藉的方法……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对于需要健康而乐观的人生观为基础的建筑艺术,是不能十分契合的。”因此,在计成和文震亨的著作里,有太多的“纯粹唯心的说法”。例如短短的一篇《园冶》,竟有大量的篇幅发为荒唐的无病呻吟和酸腐的陈词滥调。谈借景,谈到了“物情所适,目寄心期”这样虚幻的话,最后索性来一句“因借无由,触情俱是”,把环境设计的大道理又一笔勾销了。
文士心弦过度文学化的另一个痼疾是夸大。汉先生引了《长物志》中的“水石”一段话,然后说:“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若不是有精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因此,所谓造园,不过是一种布景艺术。“就环境设计而言,到了这一步,已经‘入邪’,其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了。”
总之,沉溺于文学化、艺术化的“梦境”或“遐想”,是都不可能建立建筑学的。我想,如果我们现在还用文学化和艺术化的心弦去和鸣那些“梦境”和“遐想”,大约也会成为孤独的伤感者。
汉宝德先生的这篇《明、清文人系之建筑思想》,有他独特的视角,有深刻的分析,有清新而明快的见解,更重要的是有生动的启发性和挑战性,正好台湾在七十年代初还只有几本老书可看,所以,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好几位台湾建筑学术界的朋友对我谈起过当年读这篇文章时的兴奋情绪。但是,汉先生下手的题目是对明清两代建筑的评价,虽然说到了一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问题,毕竟没有在中国建筑史上全面展开他的观点和方法,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就这篇文章讨论的题材来说,我觉得,汉先生本来还是有可能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他提出来的建筑史学的两个根本问题,即价值标准的问题和学术体系(或者说构架)的问题。如果汉先生不限制在几个文人的书本思想上,而是也把明清两代江南地方建筑在各方面的实际进步摆出来,加以探讨,看它们怎样“满足了当时社会群众的需要”,那么,我想,他就有讨论那两个问题的更广阔的天地了。
汉先生当然洞察这些遗憾之处,因而写了《明、清建筑二论》中的第二论:《明、清建筑的形式主义精神》。这一篇文章也同样地机智敏感,同样地富有独创性。尤其在第二节里,圆熟地运用他提倡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对明代以来宫殿和庙宇的发展作了非常精辟的解释,发人所未发。但是,这篇文章以反对结构的机能主义为主要目标,题材是明、清两代宫殿和庙宇的大木作和色彩等等的演变,虽然在价值观的阐发上更加具体细致,但局限性太大了,并没有能弥补第一论的弱点。
明清时期江南建筑与唐宋时期的北方官式建筑的比较,大概多少有点像古希腊普化时期北非和小亚细亚沿海城市的建筑与古典时期雅典的纪念性建筑的比较。有些建筑史家,把满腔热情的颂赞之词在雅典卫城建筑群上用完之后,对普化时期的建筑不屑一顾,说它们柔弱、僵化、冷淡,等等。然而,正是在普化时期的新兴城市里,出现了许多新类型的建筑物,有些老类型也有了新型制,结构技术有了发展,对功能的推敲深入了,构图多样化了,艺术手法也翻新了。况且出现了一些建筑著作。虽然没有产生出像雅典卫城那样艺术上完美的建筑群,但从建筑的整体上看,从全面看,普化时期的建筑成就大大超过了古典时期,正是这时期的建筑,成了伟大的古罗马建筑的直接先驱。没有它们,古罗马建筑难以到达那样辉煌的高峰。

元代王振鹏绘制的《龙舟夺标图》(局部)。它描绘的是北宋崇宁年间 (1102-1106年)每年皇室在宫廷后苑金明池举办龙舟竞渡的盛大场面。画上可见宋代建筑(来源:minghuaji.dpm.org.cn)
如果承认明清江南地方建筑的历史意义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北方的官式建筑,那么,明清两代建筑史的现行体系就得改变。如果承认中国建筑的地方性和多民族性,整个的体系就得改变。现行的中国建筑史体系是大致按照正统的二十四史断代,每个时期都是不变的几节:城市、宫殿、庙宇、住宅,等等。明清江南建筑的进步,只在“概论”里提一提。地方性和民族性,都只不过是明清住宅的“多样性”而已。地方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没有进入视野。甚至可以说,建筑的地方性的研究大约还没有开始:我们至今没有像语言学者那样,去划分中国的方言区,弄清各地方言形成的机制、特点和相互影响。民族性的研究也一样。
现行的中国建筑史体系是一个汉族本位的、官式本位的体系。这是一个按年代分门别类介绍古建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一些重要的史学内容不大可能展开。不突破这个体系,中国建筑史恐怕不大容易有突破性的进展,篇幅扩大,无非是史料增多而已。
总之,搞建筑史的人,最好还是常常讨论一下史学、史观、史法为好。汉宝德先生的著作的一项重要价值,就在于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很有独到之处的见解。我希望见到大陆上的建筑史家们,也能写些史论文章。
原标题:《旧锦新样 | 陈志华:读《明、清建筑二论》》
阅读原文
版权所有:开云体云app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沙路283号广东天健家居装饰广场G3区自建房屋(自编G341、43号)